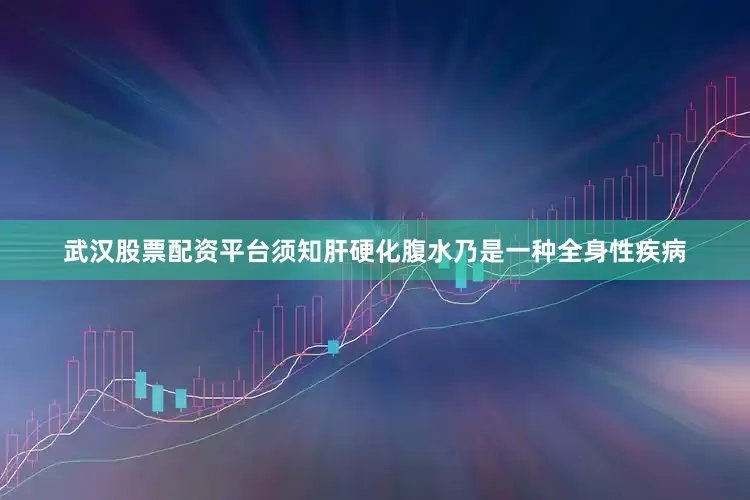
临证辨误录
作者/陈继明 讲述,朱步先 整理
本文摘自《中医杂志》(1981)
介绍:陈继明(1919—1989) 男,字浩,江苏省南通如东县人,主任中医师,江苏省名老中医。高小毕业即随父陈朗清学医。1936年以同等学历应试中国医学院被破格录取插班二年级;1950年迁居南通市设诊,翌年参加南通市中医进修学校,系统学习西医理论。1952年与朱良春等人创办中西医联合诊所;1987年被聘为南通市中医研究所顾问。撰著有《肝炎与肝硬化的中医辨治》等。

医疗经验从何而来?平时披览群书,博采诸家,此从间接来;临证细心揣摩,分析成败,此从直接来。余临证四十余年,所遇疑难杂症,若能一见便洞察幽微,药到病除者,实属寥寥;而由辨证粗疏,药难奏效,从中汲取教训,获得成功之例则较多。深感才疏学浅,未能一矢中的。兹择病例数则,就正于诸同志,对后之学者,临证少走弯路,或将有助云耳。
一、肾虚臌胀,肝脾论治无效,当予补下启中
现代医学所称之“肝硬化腹水”属于中医“臌胀”范畴。
《内经》曰:臌胀者,“腹胀身皆大,大于肤胀等也,色苍黄,腹筋起,此其候也”。
举出“色苍黄,腹筋起”与“肤胀”相鉴别,盖示人肤胀乃气分病,臌胀则气血同病。故臌证始属病气,继则病血,再则病水,但一见腹水,提示已入晚期。迅速消退腹水,自为当务之急。
一般说来,邪实体实者,可暂行攻逐;邪实体虚者,消补兼施;脾阳不运者,实脾化水;肝失疏泄者,疏络行水;腹水而兼见胸水者,温运大气,疏通三焦;瘀结化水者,消瘀行水。种种治法,用之得当,均可奏效,然亦有不效者,须加深究。
病案1
近治严姓患者,男,62岁,患肝硬化2载余,腹水形成亦已3月之久,叠经中西药物图治,未能遏制病情发展,诊时腹膨如鼓,精神疲惫,面色晦滞,形瘦骨立,脘腹痞胀,二便艰涩,脉沉弦而数,舌光无苔,证属“臌胀”重候。
分析病机,乃缘湿热久羁,肝脾络痹,气阴伤残,癖散为臌,给予补益气阴,化瘀利水之剂。药用生黄芪、天麦冬、楮实子、泽兰、益母草、泽泻、白术、石见穿、糯稻根、郁李仁等,连进6剂,诸恙依然。
窃思药之不效,乃辨证之未准,断不能以痼疾难疗自解。乃细加推敲,忽有所悟,此肾虚臌胀之候也。病系由肝而及脾,又由脾而及肾,肾司二便,今二便艰涩如此,尤为明征。再观其形神憔悴,舌光无苔,乃病久及肾,真阴耗竭之象。然而欲填真阴,又恐滞膈碍脾,踌躇再三,乃师景岳法,用大量熟地,伍入温润益气、滋阴利水方中,补下以启中。
药用:熟地120克,肉苁蓉12克,生黄芪30克,珠儿参12克,北沙参15克,楮实子30克,猪苓12克,阿胶10克(烊冲),生鸡内金10克,白茅根60克。
连进6剂,果然二便通利,腹水竟消十之六七,而且舌润津回,纳谷转增,续予原法加减调理。其预后虽难逆料,但腹水消失,诸症改善,尚能差强人意。
此例初诊之时,囿于肝硬化一般病理表现,见肝治肝,见胀治脾,故未能击中要害。须知肝硬化腹水乃是一种全身性疾病,未有全身症状不改善而腹水能获消退者。臌胀涉及肝、脾、肾三脏,至于何时治肝,何时治脾,何时治肾,当通盘考虑,突出重点。
臌胀治肾,古人早有论述,如《内经》:“肾者,胃之关也,关门不利,故聚水而从其类也”。
其开关之法,不出温阳化气、育阴化气两大法门。一俟肾气运行,则蓄积之水液可望排除,胀势自可减缓,即所以补其下而启其中也。此以补药之体作通药之用,可施于正气将竭、病邪猖獗之危候。
臌胀用峻补,乃塞因塞用之法。张景岳谓:“塞因塞用者,如下焦气乏,中焦气壅,欲散满则更虚其下,欲补下则满甚于中,治不知本而先攻其满,药入或减,药过依然,气必更虚,病必更甚,乃不知少服则资壅,多服则宣通,峻补其下以疏启其中,则下虚自实,中满自除”。
议论寓意精深,而“少服则资壅,多服则宣通”,尤为张氏阅历有得之言,景岳善用熟地,良有以也。
二、眉棱骨痛,辨明经络所属,清降阳明有效
头痛为临床常见之证,因头为诸阳之会,五脏六腑之气血皆会于此,故外感时邪、脏腑内伤均可发生。外感头痛,多因感受风、寒、湿、热诸邪所引起,且每每兼夹为患。内伤头痛多因肝阳、肾亏、血虚、痰浊、瘀血等所致,但以肝阳上亢最为多见。因此,祛风散邪、平肝潜降为治头痛之常规。但据此治病,亦有用之不应者。
病案2
1978年3月,曾治张姓妇女,43岁,头痛已历2载,时作时辍,发时前额痛剧,目胀,夜难安寐,脉弦滑,舌质红、苔薄黄,曾经西医检查,无器质性病变,诊为“神经痛”,脉证互参,断为肝阳头痛。肝开窍于目,今目胀如此,乃肝阳上亢之明征,治从清泄肝阳着手,似无不合。
药用:石决明、紫贝齿、天麻、钩藤、菊花、石斛、白芍、白蒺藜、桑叶、丹皮等,出入为方。先后两诊,讵料服之6剂仍不应。三诊增入羚羊粉吞服,又进3剂,亦无寸功。转而细思,泄肝潜降,乃治头痛之常法,用之不应,必有舛错。
细细询问,得知其痛以眉棱为甚,且晨起口有秽味,大便经常干结,察其舌,根部黄腻,如此细究,始得其真。夫眉棱属阳明,阳明者胃腑也,今大便干结,阳明郁火上蒸,所以致痛,治不清降阳明,徒泄厥阴,故而无效。
辨证既明,处方遂定,改用酒炒大黄9克(后下),甘草6克,玄明粉5克(冲),生枳实6克,葛根12克,生石膏30克(先煎),淡竹叶12克。
连进3剂,大便畅行,头痛若失。
此例辨证之误,在于问诊之粗,一见头痛,遂治厥阴,庐山未识真面目,施治焉能得效!此例说明,治头痛一定要分经论治,若不明经络,焉知病所?近来内科医家,重视经络学说者较少,殊属憾事。喻嘉言曰:“不明脏腑经络,开口动手便错”,绝非过甚其辞。
医者如能深究经络气化之理,然后循经用药,可奏事半功倍之效。今葛根、石膏皆阳明药,用于阳明郁火上蒸之头痛有效,古人药物归经之说,验之临床,确属信而可征。
三、气虚溺血,不宜见血投凉,当予益气升陷
溺血是指小便中混有血液,或伴有血块夹杂而下的一种疾病,多无疼痛之感。关于此证的成因,《内经》有“胞移热于膀胱则癃溺血”之说,多责之于热蓄肾与膀胱,阴络暗伤所致;亦有心肝之火下注膀胱者。故以清心、滋肾、泻火、凉血的治法为主。
但火有虚实之分,临证当细为鉴别,属实火者,起病突然,尿血鲜红;属虚火者,为患已久,尿血淡红而无热灼之感。实火宜泻阳以和阴,虚火宜滋阴以和阳,此其大概,但亦有不尽然者。
病案3
1979年8月,曾治陆姓患者,男性,65岁,溺血经常举发,溲时不痛,多次检查,诊断不明,每次发作,医者辄投以凉血止血之品,有时亦能暂止,但不能根治,如此缠绵年余,转请余诊。其时面色萎黄,倦怠无力,除溺血外,午后低热,体温38℃左右,口渴思饮,脉洪大,舌质嫩红、苔薄白。小便化验报告:红细胞(+~++),白细胞偶见。
初以为出血已久,肝肾阴伤,投清滋肝肾之剂,药物如生地、白芍、阿胶、龟板、女贞子、墨旱莲、玄参、小蓟、牡蛎、血余炭等,进20余剂,病无进退。
乃追根溯源,细加辨析,视其面色萎黄,倦怠少神,脉虽洪大,重按无力,均属气虚之征。至于口渴、舌质嫩红,乃气不化津,津不上承之故,与阴伤津少不可同日而语。低热见于午后,阴虚为多,但气虚亦可发生。
此患者年逾花甲,素体中虚,复进寒凉之品过多,以致中气愈陷,气不摄血,故溺血不止,改投补中益气汤加味。
药用:炙黄芪15克,党参12克,白术10克,当归10克,炙升麻6克,柴胡6克,炒陈皮3克,甘草6克,茯苓12克,仙鹤草15克,红枣5枚。
5剂溺血即止,低热亦退,精神转振,嘱服补中益气丸巩固疗效。
此例初诊拘泥常法,见血投凉,虽在辨证上已分清虚火实火,但却未见气虚一端。可见医者不仅要知其常,尤当知其变,溺血因于气虚,并非临床罕见,其中机理,当细细参悟。
夫气与血,本相须而不可须臾相离者也。中气不足之躯,气失固摄,血焉得不渗溢外出!且经谓:“血脱者,色白夭然不泽”,亡血之人,血虚则气无所附,则气亦虚;气愈虚,则提掣无力,出血更难控制。故血证经久不愈,当顾及气。
昔薛立斋治一妇人尿血,久进寒凉止血药,三年未愈,先生认为:“此前药复伤脾胃,元气下陷而不能摄血也。”用补气摄血法而治愈,对余治疗此证启迪良多,足见古代方书不可不读。
四、经前腹泻,责之冲任为病,活血祛瘀奏功
腹泻一证,其为病或因外感时邪,或因饮食不慎,但均以损伤脾胃为主要病理变化。盖脾伤则运化无力,于是胃中水谷不分,併入大肠而腹泻作矣。无怪乎张景岳说:“泄泻之本,无不由乎脾胃”。
慢性腹泻多由急性演变而来,以虚实错杂为特征,临证当详加审察,既不能畏虚以养病,亦不可攻邪以伤正。脾虚及肾者,可补火燠土;脏寒肠热者,可温脏清肠;因情志触发,肝木克土者,可扶土抑木;久泻成积者,可补虚搜邪兼进,种种治法,不可尽述。但亦有病根不在仓廪之官者,守此诸法无效。
病案4
1978年4月,余治王姓妇女,42岁,患腹泻3年,时作时愈。西医诊断为“过敏性结肠炎”,用多种西药治之不应,中药则以温肾补脾着手,亦苦无疗效,转求我诊。其时腹泻一日2~3行,便后有粘液,少腹隐痛,面色青黄,脉虚弦,舌苔薄白,断其为肝木克土。予痛泻要方加潞党参、乌梅、木瓜、煅牡蛎、木香等,先后进20余剂,有小效,但仍时作时止,不能根治。
于是详审病情,上下求索,得知其经前一周腹泻更甚,一日4~6次,经来少腹冷痛,经行夹有血块,行经后腹泻减轻,日1~2次,偶亦有大便成形者。察其舌质暗红,有瘀斑,诊其脉弦而有涩意。因思一派瘀阻胞宫之象,何不用活血化瘀药以图之?
考王清任有膈下逐瘀汤,此方可治“泻肚日久,百方不效者”。
爰用其例,予王氏原方(炒五灵脂、当归、川芎、桃仁、丹皮、赤芍、乌药、元胡、甘草、香附、红花、枳壳)。连进5剂,经行腹中冷痛已罢,腹泻亦止,三载宿疾,竟告痊愈。
此例初诊之时,误于见泻治泻,未审病源。古人云:“妇人尤宜问经期”。经水不调而致他病者,当以调经为先。《金匮》水气病在论及妇人病水时,曾有“经水前断,后病水,名曰血分,……先病水,后经水断,名曰水分”的论述。
虽系对水气病而言,但水与血之间的辩证关系,则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。经前腹泻,张石顽认为:“脾统血而恶湿,经水将动,脾血先注血海,然后下流为经,脾血既亏,不能运行水湿,所以必将作泻”,其亦指脾虚而言;而王氏之方,则指瘀血实证,旨在祛瘀以整肠。
然此法不可孟浪使用,若久泻不止,不辨气血,不明虚实,辄投祛瘀,则非王氏本意。此证用活血化瘀药以止泻,是否与其能调理冲任,纠正内分泌功能之紊乱,调节阴阳平衡有关,很值得进一步探讨。
以上四例,均属初诊未当,幸能及时改弦易辙,获得效机,从而深感辨证论治之不易。若辨证稍有差异,立法用药,自难中的,可见辨证论治乃祖国医学之精髓。我在临床带教中,发现同学能初步掌握辨证论治者固多,而对症治疗,头痛医头、脚痛医脚者亦复不少,殊堪引起重视。
当然,要做到辨证论治准确,必须打下扎实基础,常怀不足之想,日求精进之心,即以上述四例而言之,本人亦自愧学验之不足,辨证之粗疏,故加申述,以为今后临床之借镜。
怎么申请股票杠杆交易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





